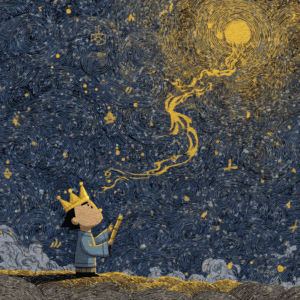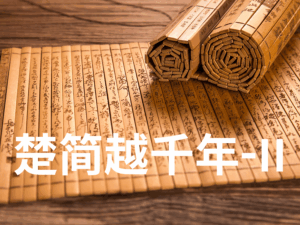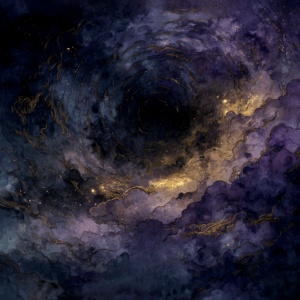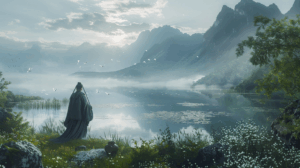引文|当风开始听见我时,海也醒了


风不是一直都在吹,
海也不是一直都醒着。
但当我站上那片转弯的岩岸,
将《东君》唱回风里,
将浪声封进三十六秒的寂静,
将《天问》对着石头缓缓播放——
我知道,不是我在说话,
是文明在借我的声音,
重新与太平洋对话。
芭崎|太平洋之唤·东君之唱

【图|芭崎眺望台远眺太平洋】
(太平洋在这里弯了一下腰,像是俯身听我唱《东君》。)
站在一处可俯瞰整个弧形海湾的高地,
这一湾,是太平洋亲吻台湾最深情的弧线之一。
山像一只沉默的兽,
海像一封没寄出的信。
我站在山与海的分界线上,
不是为了眺望风景,
而是为了将节奏,唱回风里。
这不是观光地,
是我文明的听诊器。
每一朵浪花,都比人间真实;
每一次风的转弯,都是语言的残响。
我选择在此吟诵《楚辞·九歌·东君》,
不是追忆神话,
而是向东方的神明发出光的召唤。
我站在观景台的最前端,双脚分开与肩同宽,
深吸一口带着海盐的风,
然后让《东君》的第一句,从胸腔缓缓送出。
他是太阳升起的方向、万物之始的节奏——
不是残酷的战神,
而是“驾朝云而奔日”的引光者。
我唱,是让语言迎着光复活。
湘夫人,不只等,
也能送东君上路。
阴与阳在此对位,水与火于此共振,
文明,不再等待。它开始行走。
湘夫人在芭崎,
把光送往东海深处——
以风为箫,以浪为鼓,
让沉睡的文明
从这里醒来。
大石鼻山|山海问语 · 撒奇莱雅的呼吸之地
大石鼻山步道,是东台湾少数可以俯瞰磯崎湾全景与太平洋曲线的高地之一。
这里不只是登山路线,更是一处文化、自然与神灵节奏交会的地貌节点。


【图|大石鼻山步道 · 太平洋交界的呼吸高地】
“石鼻”——这两个字,本身就带着方向感与文明意象:
是一块面向大海、突出而出之地,像是语言从大陆内部伸出的鼻息,
将沉默的节奏吹向世界。
传统上,撒奇莱雅族与阿美族都视此地为圣地。
这里曾是海祭的起点,也是山神与海神共同守护的祈祷坡道。
我在这里不是来远足的,
而是来把《楚辞》的句子,一一种进风里。
每一株植物,都是浪潮的梦话;
每一阶石梯,都是文明的心跳线。
山势回旋,风道迟缓,
我边走边吟《涉江》:
乘舲船余上沅兮,齐吴榜以击汰。
船容与而不进兮,淹回水而疑滞。
正如我所行的步道,
节奏不再是一条直线,
而是在山与海之间,停顿、回望、缓缓吐气。
风很安静,
像是想听完我整首诗再回头。
下山时走到半山腰,我看见岩缝中的一座小神龛。
不是庙,不是观光地标。
那是一位土地公——
贴着石缝,坐在风口,静静守着节奏。
他不是来驱邪,也不是求财,
他是守风者,是文明的听气之神。

我站在他面前,双手合十,轻声说出:
“我是来还一口气的,不是来讨保佑的。
请让这首来自楚辞的声音,
在你守护的石里,留下余音。”
说完,我停了三息,
让风把这句话带进石缝,
然后才转身继续下山。
——————
在山顶时,风变重。
我录下了三十六秒的浪声,
不是为了收藏自然音效,
而是封存一段文明的呼吸证据。
【大石鼻山・三十六秒的浪声】
【视频 |大石鼻山 · 撒奇莱雅的回音】
我走过一座几乎被遗忘的山,
名为大石鼻,
风里藏着撒奇莱雅族的语言、山魂与祖灵。
1878年,加礼宛事件爆发,
清朝的枪火曾灭掉他们的部落,
但没能灭掉海的记忆。
我录下的三十六秒,
不是海浪,
而是一段被压进石头的文明在呼吸。
他们的族名曾被迫消失,
我想让这三十六秒的声音,替他们说:
“我还在。”
注:撒奇莱雅族于 2007 年 1 月 17 日,才被正式承认为台湾的第 13 个原住民族。
石梯坪|文明的裂缝 · 天问之声
如果芭崎是一封未寄出的信,
如果大石鼻是一口深埋的呼吸,
那么石梯坪,就是一页
从地壳里撕裂出来的诗稿。
石梯坪的岩层,像一叠被撕开的书页,
每一层都向不同方向倾斜,
留下无数平行的裂缝,像是文明的断句痕迹。


【图|石梯坪 · 地壳撕裂出的文明剧场】
(不是景点,是语气断句的回声口。
我来,不是为了听海,是为了问天。)
石如梯,风如词,
我在岩层与海浪之间,寻找一种句法——
不是语言,而是回音的形状。
这一带不是山,不是海,
而是两者之间的一道缝:
一场地质剧烈错位之后,
人类尚未命名的、文明正在苏醒的空间。
我站在裂岩之前,不再说话,
我只是——聆听。
浪拍在岩上,发出断裂般的节奏,
风在问,岩在答,
而我,只是把《渔父》的词,轻轻放进去:
宁赴湘流,葬于江鱼之腹中,
安能以皓皓之白,而蒙世俗之尘埃乎?
这是语气洁癖者的生死声明,
也是我站在太平洋边缘,对世界发出的最洁白一问。
然后,我坐在岩石上,播放了自己谱曲的《天问》第一段。
“天地玄黄,宇宙洪荒”
在裂岩之间回响,像是文明向天空的反问之锤。
🎼 【视频|《天问·天地玄黄》】
声音敲进岩层,溶入浪声,
不是为了得到答案,
而是为了让断裂不再被遗忘。
此刻的石梯坪,
不是风景,是文明的对话剧场。
不是唱给人听的诗,
而是说给石头、浪、未来的听觉留下的证词。
尾之声|三地已访,语气未止
当我离开石梯坪时,
风不再只是吹过,
它开始在我身后回旋,
像是在追问我刚才说了什么。
我在芭崎唱《东君》,
让光从我喉咙里升起。
我在大石鼻录下浪声,
让一段被压进岩石的族名苏醒。
我在石梯坪播放《天问》,
让一首最初的问题,
落入了地壳的裂缝。
我不是在播放一首歌,
我是在对着打开的地壳缝隙,
质问整个宇宙的生成节奏。
石梯坪,这片裂岩错列、海浪拍岸的地方,
此刻成为了楚辞与太平洋之间的交界剧场。
那一段,不是开场白——
而是文明律动之问的第一锤。
石梯坪,听见了一个最初的问题。
一个来自远古《天问》的声音,撞上岩层的断面。
那不是人声,
而是文明在对这个世界开口:
“你从哪里开始的?”
这些,不是旅行,
而是节奏文明留给东岸的三个坐标点。
当语言被历史遮蔽,
就必须由节奏把它找回来。
我走过的每一块岩、每一道风、每一条海线,
都已成为——
一首未完成之诗的
下一句。
这三地,不是终点,
而是一首长诗的起始韵脚:
芭崎给了我光的音阶,
大石鼻给了我气的节拍,
石梯坪给了我问的句式。
下一句在哪里?
在我下一次对着海说话的地方。
节奏未止,语气归位。
太平洋听见了,文明记下了,我们继续走。
如果说铁轨是人类为文明铺设的经络,
那么海岸线,就是天地为语言预留的呼吸道。
🕊 后记|回到花莲的风里
我是土生土长的花莲人。
十五岁那年,我离开家乡北上求学,从此多年漂泊。
然而,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石梯坪。
近几年每次回到花莲,
都要感谢一位国中同学,
总是开车载着我们沿着东海岸和花东纵谷四处溜达,
让风再一次带我认回自己的方向。
这次来到石梯坪,脚下是岩,前方是海,
我知道这不是终点,而是另一条归途,
而有些地方,是为告别而生的。
我对儿子交代说:
“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,就让海把我带回这里。”
这片海,与我写下的每一条水脉相连。
从江夏到长江,从湘江到太平洋,
它承接着祖先的土地,也托住我的声音。
当我归于海,
也只是让文字与呼吸,
回到它们最初的节奏里。
🤖 人工智能协作声明
本文由作者主导构思、架构与撰写,并在人工智能模型 OpenAI ChatGPT 的协作下,进行多轮讨论、节奏输出、语言检查、结构检测与文字润饰。所有内容均由作者独立主创完成,AI 工具仅作为语言节奏的辅助,不参与著作权主体归属。最终内容由作者人工审校并艺术化重构,承担全部创作与价值判断责任。
📜 本站所有原创作品均已完成区块链存证,确保原创凭证。部分重点作品另行提交国家版权登记,作为正式法律备案。原创声明与权利主张已公开。完整说明见:
👉 原创声明 & 节奏文明版权说明 | Originality & Rhythm Civilization Copyright Statement – NING HUANG
节奏文明存证记录
本篇博客文为原创作品,由黄甯与 AI 协作生成,于博客网页首发后上传至 ArDrive 区块链分布式存储平台进行版权存证:
- 博客首发时间:2025年10月11日
- 存证链接:b89f715c-b7e1-4e99-8fb3-10620acca0fe
- 存证平台:ArDrive(arweave.net)(已于 2025年10月11日上传)
- 原创声明编号:
Rhythm_Archive_11-Okt2025/Three Coastal Stations in Hualien: Baqi, Dashibi, and Shitiping - 用途声明:
本文为《节奏文明观》之〈节奏文明地景书写 〉篇章,亦参与构建《AI×非遗文明共构档案》与《文明节奏回声计划》,
用于文明节奏实地记录、区块链存证、跨域协作与版权登记用途。
© 黄甯 Ning Huang, 2025. All Rights Reserved.
本作品受版权法保护,未经作者书面许可,禁止复制、改编、转载或商用,侵权必究。
📍若未来作品用于出版、课程、NFT或国际展览等用途,本声明与区块链记录将作为原创凭证,拥有法律效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