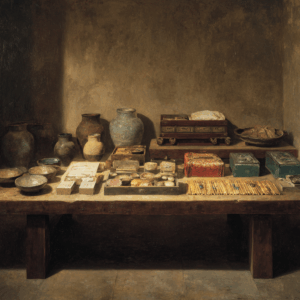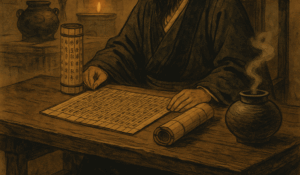引文|在海与石之间,听见身体的回声


花莲是一首长诗。
风从太平洋的尽头吹来,带着盐与光,
拍打山脚,也拍打心底。
七星潭的浪花不说话,
却一声声打在身体里,
像远古留下的节奏,仍在日夜不息。
这里,身体先于语言——
在毛月亮的月色下起舞;
在鱼市的清晨中呼吸;
在庙宇的香烟里低头;
在工厂的轰鸣中安放。
每一声,都有节奏。
每一次切石、每一阵海浪、每一次祈祷,
都让人重新感到:
文明,不只是书写的文字,
而是身体与土地之间,
那一段仍在回响的气息。
若说海与山是花莲的骨骼,
那么舞者的身体,便是那骨缝间最柔的光。
——光将起舞,节奏即将被唤醒。
一、毛月亮|身体与月光的节奏


她起舞于月下,跳出身体未被命名的节拍。
——在手机毁掉三代人的时代,一万个人席地静坐,只为看舞、看月。

这不是演出,而是一次文明的体温测试
这⼀夜,没有抢位喧闹,没有闪光扫过人群,没有荧幕高举遮挡视线。
因为云门舞集早已明文规定:全程禁止摄影与录像。
观众应允、配合,无需提醒,手机安静地留在口袋里。
这不是因为没人想记录,而是因为这一场,值得我们只用眼睛、耳朵与身体去记住。
当一万人选择在田径场草地上静静坐下,
当全场顺从节奏的呼吸与律动,
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文明深层的同步试炼——
不是“观赏”,而是“共在”。
太平洋旁的田径场,此刻成为神话的剧场

花莲的海风从后侧吹来,月亮悬于高空。
镜面舞台上映照着扭曲的兽形与人性的身影。
那不只是肢体,而是一场关于爱、争夺、孤寂与渴望的远古共振。
田径场,曾是竞赛之地,
今晚却成为节奏记忆的仪式现场——
舞者如图腾伏地,观众如部族席坐,
一同进入一种“被召集”的时间。
毛月亮:不是诗意,而是徵兆
“月暈而风”,古语早有记载。
这夜的《毛月亮》,不只是月象,也不只是舞作名称,
它像是一道来自未来的气候徵兆——
提示我们:节奏即将转变,有事将发生。
郑宗龙将极地音乐、镜面结构、纸雕幻影与兽性动作,
编织成一齣非线性的神话舞剧。
观众不再追问剧情,而是回到一种古老的身体阅读法:
在风中察觉、在光中辨形、在集体静默中,
感知我们仍能共振的能力。
文明没有死
在这个被手机切割成碎片的时代,
我们常说 “文明正在衰退””人心已被毁损”……
但那一夜,我带着父母与儿子,四人一起走进花莲田径场,
坐在草地上,没有拿起手机,没有说一句话,
只是静静地,看风,看月,看光。

三代人,就这样坐在节奏的中轴线上,
像部族一样,一起等待舞者奔入神话,
一起,在身体的呼吸里,确认文明尚未死去。
你若问:文明还在吗?
我会说——
来过花莲这一夜,就会知道,文明还没死。
——夜的节奏落幕,清晨的呼吸登场。文明的体温,从舞台转入海口。
二 、花莲渔市|清晨的劳动与盐的味道


当鱼不再卖,鲸也不再来,节奏滞留在港口之间。
节奏停滞的海口
这不是我记忆中的鱼市了。
昔日船只归港、鱼货上岸、叫卖声四起的节奏,
如今主要被鲸豚观光取代,
却又因太鲁阁封闭、震后重创,陷入停滞。
赏鲸船依旧停泊,但是旅客寥寥。
码头不再叫喊,只剩关闭的店家,
像是一场早就收摊的文明表演,
还来不及谢幕,就被遗忘在潮汐之外。。
城市节奏的延迟
花莲,太久没有变化了。
如一首单调重复的鼓点,
没有加速,也没有重拍。
游客来了又走,
许多的观光景点,
都像是等不到下一波海风的船,
静静发锈。
我想起台东——它正在赶上来。
池上稻田、温泉、展览、咖啡馆,
台东的呼吸有节奏,
而花莲的喘息,仍滞在原地。
港口不是终点,而是文明的隐痛
渔市,不再卖鱼;鲸船,接不满人。
港口留下来的,只是“曾经很热闹”的痕迹。
这是花莲正在经历的:
节奏失序后,没人负责恢复拍点。
没有人问,这些港口还想说什么;
也没有人听,它们此刻正在沉默。
——当城市的节奏慢下,海仍在拍打时间。
于是我往更静的地方去——七星潭。
三 、七星潭|湘君奏于七星潭,风与石为证


浪一层一层,打在石上,也打在时间里。
骑车前往,召唤在途中启动
我骑着摩托车,往七星潭去。
没有特别的理由,只是身体知道要停下。
于是我坐在海边,把自己谱曲的《湘君》,放给太平洋听。
不是为了谁听,
只是风刚好在,海也刚好在,
而这首歌,该在这里被听见。
这不是音乐,而是一种召唤
我坐在砾石堆上,
让风灌进耳朵,
让那旋律从手机传进空气,也传进骨头。
头顶一架又一架 F-16,从花莲空军基地飞过,
轰隆如雷,金属掠空,
像是现代军神在演奏速度的力量。
但就在某一瞬,
一个浪盖过了飞行的轰鸣,
像是海,以自己的节奏,温柔地干预了那场节奏的暴力。
我低头拾起三颗石子,
一颗是小时候,
一颗是未竟的乡愁,
一颗是古老山神没说完的话。
我把它们叠起来,静静地说:
“这里,湘君和湘夫人来过。
风知道,海知道,石也知道。”
山神留下的碎白

沙滩上散落着一堆木头,
它们是暴雨之后,从山里冲下来的记忆。
那不是漂流木,
那是山体把未竟的故事送入海中,
再让海把它们拋回陆地。
它们没有成舟,也未成像,
只是静静躺着,
像湘君奏毕之后,山神留下的碎白。
我坐在沙上,用指头写下两个字:
“还魂“。
没有仪式,没有祈请,
我只是让浪潮,决定它要不要留下。
——从海的咸味,转入米的甜香。节奏开始在土地深处发酵。
四、 花莲观光酒厂|米是慢的,玉是静的:米酿汤,玉藏心


米在酿汤,玉在沉香。时间在这里不语,却余韵绵长。

在酒厂里,我咬下一口红麴绍兴香肠,
香气是热的,生意却冷了。
自从大陆观光团不来,这一带的空气更显寂静。
但花莲人的手,仍在做事。


我在观光酒厂的一角,
发现一桌花莲玉与丰田墨玉——
不是在玉石工坊,
也不在文创园区,
就藏在贩酒的空间里,
灯光下,静静闪着微光。
那一刻我想起,
我手上常年戴着的手链,
正是花莲玫瑰石制成的。
不是刻意挑选,却总在身侧温润。
或许冥冥之中,
我承袭了楚人爱玉的习惯,
也携着这份温柔,走遍山河。
玉器没有声音,
却很有气味:
温润如米,
沉静如山。
我没有买酒,因为家里有。
但我挑了两支黑色墨玉的刮痧棒——
那是我每次回台湾都会带回德国的东西。
送人也好,自用也好,
那不是礼品,
是我从土地上雕回的身体记忆。
每次回花莲,妈妈总会煮一锅米酒头鸡汤,加鱼腥草叶。
那不是菜谱,
是花莲的体温,是中央山脉的气味。
这不只是一次返家,
而是一种被慢火酿出的文明回声——
米是慢的,
海是蓝的,
玉是静的,
而家的味道,
是静静发酵出来的。
——离开酒香,我走向木香。那是另一种发酵——记忆的发酵。
五、 将军府|日式木屋的回声


木窗的裂缝里,住着将军的余音与记忆的风。

松树的清香,
曾沿着美仑溪的水气,慢慢渗进屋瓦,
在低檐与木造之间,
留下了那一段日据时代的呼吸。
格子窗内,
曾有榻榻米与推拉门,
将光线分成柔软的格子。

我记得,
小时候趴在榻榻米上的午后,
手掌贴着草编的纹理,
鼻尖闻着松香、七里香与阳光交融的味道——
松树清凉、花香微甜,
混着热空气里的光影,
让呼吸和心跳一样缓慢。
如今木格窗后是咖啡与人声,
榻榻米化作记忆中的一张席;
门前的松树还在,
枝影投向小径,
仿佛在与山坡上的“松园别馆”对话,
彼此守着同一片太平洋海风,
也守着那份不会退色的年代气息。

对我来说,
这种日式木屋与榻榻米铺成的空间,
是台湾土地上最真实的成长记忆。
我就出生在这样的校园宿舍、这样的木屋走廊之间。
那是一种踏实的温度,
不是异国风情,
是童年留下的——土地的味道。
——从木屋的静谧,到白墙的慈悲,
呼吸换了形态,却仍在同一条风里。
六、慈济|悲心与智慧的相遇之地


诵经声中,人间的病痛与慌张悄然安歇。

在太平洋的风声中,
花莲慈济医院矗立如一盏白色的灯,
迎来无数寻医的脚步,
我亦曾多次来此,
就诊于眼科李医师。
这里不仅有精湛的医术,
更有一份安抚人心的柔光。

顺着左侧的道路缓缓步入静思堂,
屋檐高翘、石阶宽阔,
像一双慈悲的手,
静静托起人间的忧与苦。

堂内木香温润,
长廊两侧挂着慈济人走遍世界的影像:
救灾、义诊、助学、环保——
一张张照片,
串起一条延伸至无边的菩萨道。


墙上题着的字句:
“心包太虚,量周沙界”
“一为无量,无量为一”
像是静思堂的心跳,
提醒每一位来者:
疗愈,并不仅止于肉身,
更是修补生命的缺口。
在这座海边小城,
花莲慈济守护着一种信念——
让悲心成为行动,
让智慧照见众生。

——医院治身,庙宇治心。
文明的修复,仍在继续;
风从海面吹来,
带着经声的余温,
也轻轻吹向丰滨的山。
七、女娲娘娘庙|补天之处,补文明之心


她不是神话,她是风中低语的母音。

我们一家人走进女娲庙。
不是来祈愿,
而是来回应。
石阶一步一步,
像走回洪荒之后的第一场寂静。
我在门口深呼吸三次——
不是为了平静,
而是为了让自己的气息,
与那场补天之力对上频率。

天曾裂过,
大地曾沉,
文明也曾在缝隙中失落。
香火的热气像岩浆从地心涌上,
木柱吱呀,像巨石被重新推回天穹。

我抬头望见她——
女娲的眼神,
不是慈母的安抚,
而是匠人与守护者的锋光。
我在心里问:
“你补过的天,
如今又裂在哪里?”
风声、海声、石声,
一声声回应:
“裂在人心之间,
裂在文明记忆里。”
在庙里,
没有许愿,
而是留下一个承诺——
当天裂时,你补;
当文明裂时,我愿写下它的缝痕。
用文字、用歌、
用脚下的每一步,
将这片土地的节奏,
一针一线,
缝回天地之间。

在离开时,我拾起一片落叶,
轻轻放在她金色的尾鳞上——
像是为那尚未补完的裂缝,
暂时覆上一层自然的温柔。
那不是冒犯,
而是一次静静的缝补仪式。
用一片叶子的轻,
回应那万钧的重。
——————
走下女娲庙的石阶后,
父母开车载我们去盐寮。
风吹起一身香火气,
肚子也跟着空了。
于是我们转进 055 龙虾餐厅——
那是我的最爱。
补完天,也要补补肚子。
——从补天到补腹,
从天的裂缝到饭桌的笑声,
花莲的日常总能收拢庄重,
让神话落地成人间的温度。
八、055海鲜龙虾餐厅|海味记:三代共桌的晚餐


晚风送饭香,龙虾红处是人间烟火的诗行。

从庙口下来,
我们直接开往盐寮的 055 龙虾餐厅。
天色微暗,海风刚好,
店里人声鼎沸,
水族箱里的龙虾还在吐泡。

我最爱的四道菜:
清蒸龙虾、红烧九孔、凤梨虾球、还有那道家常的特色炒面。

龙虾肉质结实,虾膏饱满;
九孔上桌时酱色油亮,
一口咬下,全是熟悉的味道。
凤梨虾球酸甜酥香,
小孩吃得最快;
招牌炒面份量足、锅气十足,
连平常少吃主食的,也盛了第二碗。
这顿饭没多讲什么,
却让人记住了晚风、
海味、
和那种刚刚好的满足。
——夜的热闹散去,山的呼吸重新显影。
节奏从海回到林,
文明的旋律,正缓缓换气。
九、林田山林场|山与人之间的劳作记忆


锯屑未落尽,山林仍记得工人的合唱。

这里曾是台湾第四大林场,
日据时期开始伐木,
全盛时号称 “山里的小上海“。
直到1987年禁伐,
一切归于静默。
再次走进这座沉睡的林场,
不只是来看风景,
而是来 “听“。


中山堂,像一座失声的剧场,
那排日式檜木宿舍,
像时间折叠的信封。
它们不是建筑,
而是呼吸过的身体。

终于找到了加藤机车,
站在它面前,
我说:
“我知道你载过的,不是人,而是树的灵魂。”
然后轻声补上一句:
“魂兮归来,车头还在等你。”

我闻到林场里那股熟悉的檜木味,
不是香气,
是历史曾鲜活的味道。
像千万片木头剖开的刹那,
那些人的日子、语言、汗水,
都还在。

就在我走近米店时,
一位原住民工作人员对我笑说:
“那个阿公,等你很久了。”
一旁的老人笑着补一句:
“从日据时代,就等到现在啦~”
当时我忽然觉得,
整个林场都在等一句话、一次回声,
等一位愿意倾听他们的人。
外面下着雨,手边没米酒,
不然真想敬他们一杯。
敬这些不说大道理,
却一直在场的工人们,
敬这些,
把历史活在自己身上的人。
——一切回到起点。
石头仍在说话,
只是声音更低、更深——
那是文明的低音,
也是我童年将要听见的回声。
十、大理石工厂|花莲的颜色:我的童年


每一层石粉,都是父母的汗水与生活的节拍。
五岁那年,
我站在卡车旁,
看深邃碧绿的蛇纹岩、和平白的大理石,
被一块块卸下来。

碧绿如海底的潮汐,
洁白如冬日的月光,
偶尔被刷上蓝色号码与红色印记,
像远方寄来的密码信,
落在我掌心的粉尘上。

📹 我录了一段 30 秒的机器切割石块视频。
那是童年最熟悉的声音,也是我记忆中最重的一段节奏。
📹 视频:机器切割石块现场
小时候,家里做多元生意。
周一到周六,我们孩子得一早四点起床煮豆浆,卖早餐。
放学回家,得照料杂货店。
到了周末,
不是休息,而是去田里帮忙,或在大理石厂工作。
我从小就开始做石工。
当时家里做的不是石板,而是整组的圆形石桌与椅子。
我的工作,是把四方石块切割成圆,打磨边角、烤火、上胶,
把转动的轮轴黏牢。
那些石粉、胶水、寒冬的烤火炉,
还有机器的轰鸣——
构成我童年的气味和声音。
这段童工经验,没有被遗忘;
它在我心里种下了一句话:
我要离开。
不是因为我不爱这里,
而是太早懂得——
背负的太多,会让人不敢停下来喘口气。
十年的石粉,
没有夺走我的指纹,
反而让它们记住了纹理的方向——
我能闭眼分辨粗砺与细腻,
听得出石头心里的那道暗河。
我学会了倾听:
重量与光泽从不自带尊敬,
它们只是石的性格,
如同人的头衔,
不过是另一层纹路。
我见过工厂里最昂贵的机器,
也见过最清淡的饭菜;
见过站在高处指挥的人,
在下班后脱下制服,
和我们一样坐在木凳上,
咀嚼酱菜与白饭。
后来做工艺,
我对材料的敏感,
比别人多出十年的重量与呼吸。
当有人用职位与身份介绍自己,
我只是微笑——
在心里默默将它,
与花莲的颜色相比,
看看哪一种更深。
小时候太累了,
那种疲惫至今还在我身体里。
但我也承认:
正因为那份累,
我后来才懂得如何倾听别人的沉默,
如何在重量里寻找真实。
这不是要美化那段日子,
而是说:
伤害与成长,
有时候,是同一件事。
——石声未歇,节奏仍在。
从山的回声,到家的脉动,
我终于听见——
文明的心跳,
在石粉里延续。
尾之声|节奏尚在,回声不止
十处地景,十段节奏。
在花莲,我听见了文明的低音。
不是在博物馆,不是在讲堂,而是在石头、浪花、香火、车头、螺丝、鸡汤与孩子吃完饭的空盘之间。
这一切,不是为表演,不是为怀旧——
而是土地在用最真实的方式,对我轻声说:
“我还在。”
在毛月亮的田径场,
我们以身体聆听月光;
在渔市与女娲庙,
我感到文明的断裂与等待;
在大理石工厂,
我听见童年的轰鸣与汗水,
仍在地底震响。
不是所有节奏都来自音乐,
有些节奏,藏在沉默里,
藏在太平洋的风与孩子的呼吸之间。
于是我写下这十部曲,
不是为了记录曾经有多美,
而是为了确认——
节奏尚在,回声不止;
身体还记得,文明未亡。
——当风再起,
海会继续拍岸,
石仍在发声。
文明的心跳,
就在此刻。
🤖 人工智能协作声明
本文由作者主导构思、架构与撰写,并在人工智能模型 OpenAI ChatGPT 的协作下,进行多轮讨论、节奏输出、语言检查、结构检测与文字润饰。所有内容均由作者独立主创完成,AI 工具仅作为语言节奏的辅助,不参与著作权主体归属。最终内容由作者人工审校并艺术化重构,承担全部创作与价值判断责任。
✍️ 本文完成初稿后,感谢德老师的细致修订与润笔。
📜 本站所有原创作品均已完成区块链存证,确保原创凭证。部分重点作品另行提交国家版权登记,作为正式法律备案。原创声明与权利主张已公开。完整说明见:
👉 原创声明 & 节奏文明版权说明 | Originality & Rhythm Civilization Copyright Statement – NING HUANG
节奏文明存证记录
本篇博客文为原创作品,由黄甯与 AI 协作生成,于博客网页首发后上传至 ArDrive 区块链分布式存储平台进行版权存证:
- 博客首发时间:2025年10月14日
- 存证链接:182edb45-7259-4ea0-a550-ac9729f2b723
- 存证平台:ArDrive(arweave.net)(已于 2025年10月14日上传)
- 原创声明编号:
Rhythm_Archive_14_Okt2025/hualien-decalogy - 用途声明:本文为《节奏文明观》之〈节奏文明地景书写 〉篇章,亦参与构建《AI×非遗文明共构档案》与《文明节奏回声计划》,用于文明节奏实地记录、区块链存证、跨域协作与版权登记用途。
© 黄甯 Ning Huang, 2025. All Rights Reserved.
本作品受版权法保护,未经作者书面许可,禁止复制、改编、转载或商用,侵权必究。
📍若未来作品用于出版、课程、NFT或国际展览等用途,本声明与区块链记录将作为原创凭证,拥有法律效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