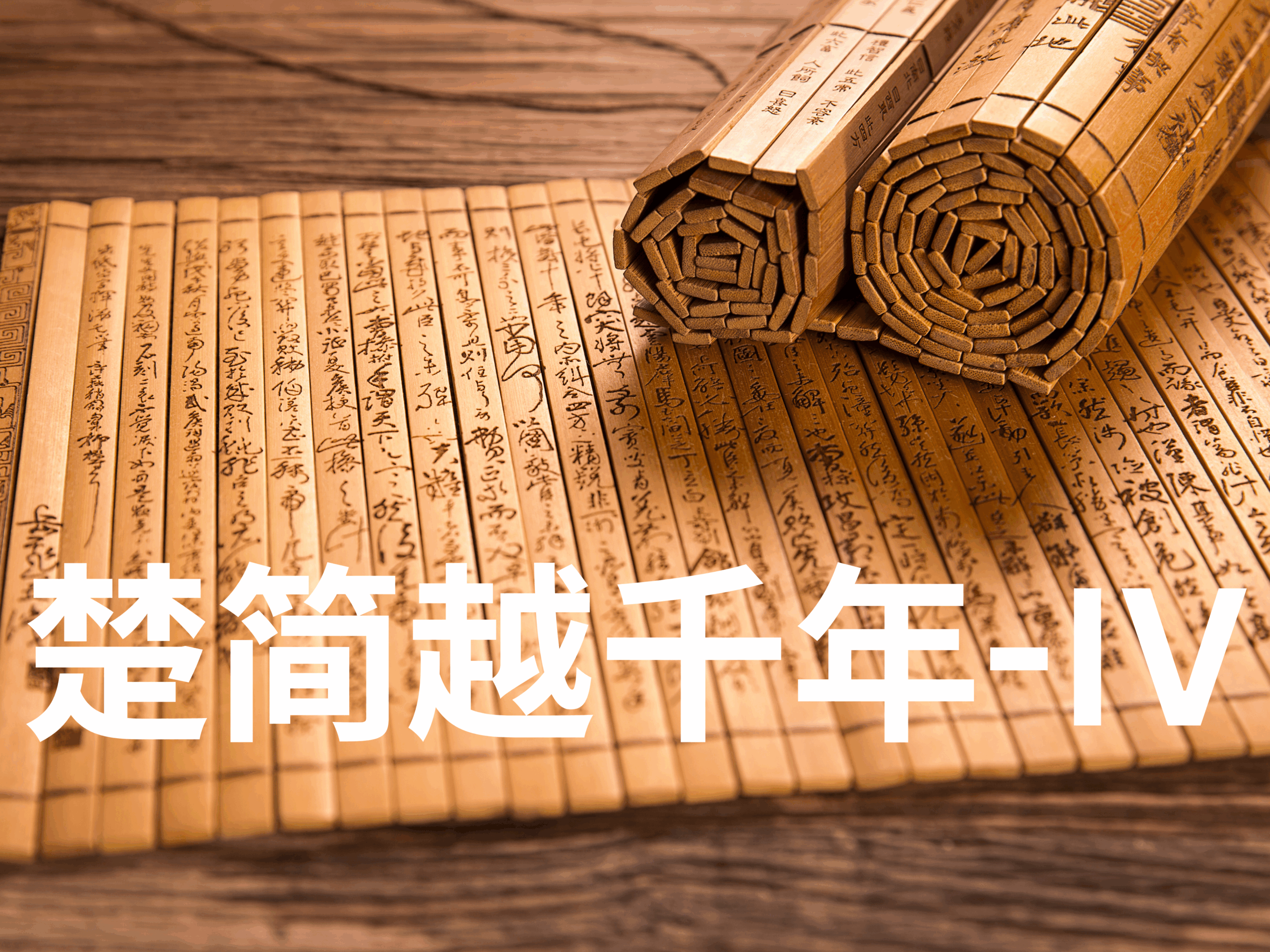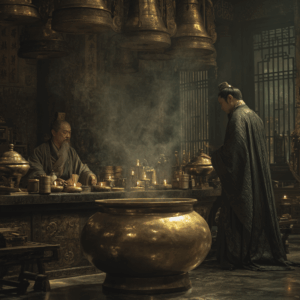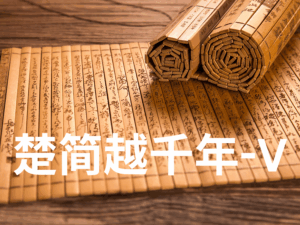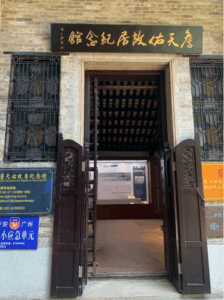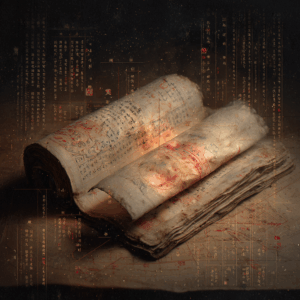两千年前沉睡于荆楚大地的竹简,记录了文字的诞生、秩序的形成与文明的延续。
五集纪录片《楚简越千年》,不是考古的复述,而是一场倾听——
听那些写在竹上的声音,如何在今天重新被读懂。
本篇为《楚简越千年》系列的第四集《一墨千秋》,聚焦楚简从学术殿堂到民间匠心的再书写与活传承机制。
从北京红楼的学者群像,到荆州潘灯、黄有志的草根坚守,再到李胜洪将楚文字带入课堂与童心,
我们看见当代之手如何以耐心与热爱,让沉睡的文字重新回到人间。
它们在指尖中获得温度,在众手间汇成节奏,以手为声,延续文明的书写脉搏。
这些被重新抄写的竹简,正悄然复原一座民间与学术共鸣的文明回声场。
引文|荆州人的手,在抄一部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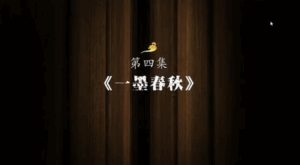
图:纪录片《楚简越千年》
不是谁发明了文字,
而是谁在灯下、在手指之间、在童年的纸页上,重新写下它。
荆州人正在这样做。
他们不问自己是不是学者,只是相信这古老的字,不能丢。
潘灯整理出六千多个楚文字单字,
黄有志以手复制竹简上的字形,
李胜洪把楚文字带进孩子的练习本。
他们是普通人,但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手,抄写一部属于民间的楚简——一部 “众手之书”。
让楚简,不再是墓里的遗物,而是人间的课本,是文明的回音。
他们不是在用嘴说话,而是用手写字——
这是文明的另一种发声方式。
手的书写,就是文明的声音。
北大红楼之后|楚文字如何浮出水面
1950年代初,为了整理新发现的战国简牍材料,
全国各地研究古文字的学者齐聚北京大学红楼——
在那里,开启了誊录、整理与比对的工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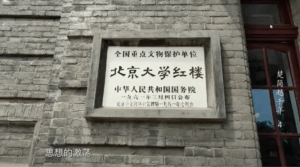
图|北大红楼(截图自《楚简越千年》第四集)
这是新中国成立后,第一次大规模协作研究战国文字,
也成为后世学界回望战国文字研究起点的重要时刻。

图|红楼学者(截图自《楚简越千年》第四集)
此后,这一阶段常被视为战国文字研究真正意义上的起点。
清华大学已故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曾回顾指出:
战国文字的系统研究,真正是在1950年代以后才逐步开展。

然而在那个年代,学界所掌握的,仍只是零散的文字残片,
楚文字的整体面貌,还远未浮现。
真正让这套文字系统浮出水面的,
是荆楚大地的古墓葬逐步被打开之后——
半世纪以来,望山、郭店、秦家咀、王家咀、包山等地大量楚简陆续出土,
人们才获得对楚文字的直观认识。
这些文字不似金文、也不似甲骨,
笔画卷曲如舞,
像是从中原法度的主流河道中,
分出的一支自由的山水支流。
楚文字填补了甲骨文与小篆之间的关键断层,
不再只是边缘的变体、杂体,
而是一套完整的书写系统,
带有鲜明的地域风格与灵动的节奏特性。
那是楚地书写者的手,
为这片土地留下的另一种秩序与美学——
不同于中原的笔直与规整,
而是带着江汉水岸的自由与流动。
近年来,战国文字研究论文数量不断上升,
楚文字逐渐成为古文字领域最活跃的方向之一。
文字的重心,
正从北方帝国的中轴,
缓缓转向南方江岸的书写地带。
文明以手为声|荆州之手三部曲
他们不是考古学者,
也不是高校专家,
却在楚简的日常修复与教学实践中,
为古文字写下了这个时代的注解。
一|潘灯:字形汇集者

图|潘灯(截图自《楚简越千年》第四集)
他用三千多册藏书,
换一部六卷本的《楚文字汇编》。
他不是大学教授,不属任何课题项目,
只是一个对楚文字着迷的草根艺术家——潘灯(本名潘传国)。
潘灯说:“我光造字就花了三年时间。”
因为学习古文字的工具书太少,
他便决定亲自编撰一本。
这不是学术规定动作,
而是一个人认字、认时代、认文明的方式。
多年来,他一笔一划绘出6286个楚文字单字,
将分布在出土材料中的字形分类、绘制、标记,
自己做索引、做编码、做释文。

图|潘灯编纂《楚文字汇编》(截图自纪录片)
墙上贴满手写字卡,
每一个字都像是他亲手从泥中捞起的痕迹。

图|潘灯工作室的字卡墙面
六卷的《楚文字汇编》,
是一套完整的楚文字检索系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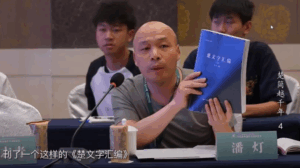
图|潘灯展示《楚文字汇编》六大册(截图自纪录片)
这不是个人的笔记,
而是一套可以进入教学、研究、再书写的专业工具书。
二|黄有志:简牍复制非遗继承人

图|黄有志(截图自纪录片)
他以手中技艺,还原古文字的形貌与神采,
为全国五十多家博物馆复制楚简。
他不是考古队员,也不是修复专家,
却被央视、清华大学、各大文博单位找上门,
只因为他复原得“像”,写得“真”。
有人寄来扫描件,有人带来原件,
他就在荆州的工作室里,
一点一笔,慢慢描摹出曾经的手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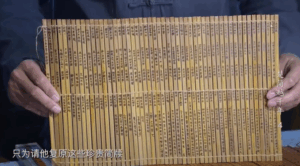
图|黄有志手工复制的楚简竹片(截图自纪录片)
他的复制本被广泛用于展览与教学,为今日文博复制提供了一种常见的楚简呈现方式。
三|李胜洪:一级美术师与教学传播者
他从书法出发,回到文字的源头。

图|李胜洪(截图自纪录片)
书法家李胜洪将楚文字用于书法教学,
他将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——
这一套我们耳熟能详的启蒙文本,
一字一字写回楚简的样貌。
他将这些内容制成字帖、教材、展示册,
用于校园教学、展览推广与学术研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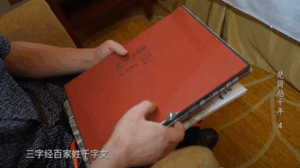
图|李胜洪楚文字书法教材(截图自纪录片)
这不是复古的练习,
而是他亲自挑选的文本载体——
最适合以楚文字再书写的篇章。
他让这些字,
从字帖走进教室,
从历史走进当代。
四、文明正在被抄写:荆州人的众手之书
在潘灯的工作室里,
新的字卡还在不断被贴上墙面;
在黄有志的案台上,
又一批楚简复制品即将送往博物馆;
在荆州的中学教室里,
学生们正用毛笔写下楚文字版的《三字经》。
在这三位荆州人的推动下,
学生们正一笔一画练习那失传已久的笔画。
他们没有统一的机构,
也没有谁下达过命令让他们去做。
他们只是默默地写。
不为考试,不为发表,
只因他们知道:这些字,若不抄下来,就会消失。
但他们不仅是书写者,
更是留下者——
留下了一批可以被继续抄写、再度流传的文明副本。
这些书,不来自大学或研究院,
而是荆州人亲手写出、自行出版、自行使用的文字集。
它们有编号,也进入馆藏,
但更重要的是:
它们是这座城市用众人之手共同抄写出来的楚文明版本——
“众手之书”。
楚简的延续,不止靠学者,
更靠那些愿意写、还在写的人。
潘灯的楚篆汇编、
黄有志的竹简复制、
李胜洪的书法教材——
这些看似独立的工作,
共同构成了当代荆州的书写合声。
他们所写的,
正是楚文字的当代生命。
尾之声|众手共抄,文明不息
这些字,曾在墓中沉睡千年。
不是因为被遗忘,
而是因为太晚被发现、还没人来抄写它们。
它们没有等到帝王,也没等到主流教材,
等到的,是一群在荆州写字的人。
他们身份各异,背景不同,
却都在做同一件事:
把失落的文字,写回人间。
他们一笔一画写的,
不是学术结论,
而是对两千年前那些写字人的回应——
你们写过的字,
我们还记得。
他们在回应泥土,回应墓室,回应那些遗简,
回应祖地,回应时间,
回应那份从简牍深处传来的问:
你们还在写吗?
你们还记得我们吗?
他们没有回答。
他们只是继续写。
写下去,
楚简就不再只是出土物,
而是呼吸——
一种在荆州人手中延续的文明气息。
文明以手为声,在此刻,回响不绝。
🤖 人工智能协作声明
本文由作者主导构思、架构与撰写,并在人工智能模型 OpenAI ChatGPT 的协作下,进行多轮讨论、节奏输出、语言检查、结构检测与文字润饰。所有内容均由作者独立主创完成,AI 工具仅作为语言节奏的辅助,不参与著作权主体归属。最终内容由作者人工审校并艺术化重构,承担全部创作与价值判断责任。

📜 本站所有原创作品均已完成区块链存证,确保原创凭证。部分重点作品另行提交国家版权登记,作为正式法律备案。原创声明与权利主张已公开。完整说明见:
👉 原创声明 & 节奏文明版权说明 | Originality & Rhythm Civilization Copyright Statement – NING HUANG
节奏文明存证记录
本篇博客文为原创作品,由黄甯与 AI 协作生成,于博客网页首发后上传至 ArDrive 区块链分布式存储平台进行版权存证:
- 博客首发时间:2025年10月18日
- 存证链接:4e7a126e-8d6d-456f-a70c-27527434f407
- 存证平台:ArDrive(arweave.net)(已于 2025年10月18日上传)
- 原创声明编号:
Rhythm_Archive_18_Oct_2025/chu-bamboo-slips-across-a-thousand-years-part-4 - 用途声明:
本文为《节奏文明观》之〈楚文明 〉篇章,亦参与构建《AI×非遗文明共构档案》与《文明节奏回声计划》,用于文明节奏实地记录、区块链存证、跨域协作与版权登记用途。
© 黄甯 Ning Huang, 2025. All Rights Reserved.
本作品受版权法保护,未经作者书面许可,禁止复制、改编、转载或商用,侵权必究。
📍若未来作品用于出版、课程、NFT或国际展览等用途,本声明与区块链记录将作为原创凭证,拥有法律效力。